Circulation:紫杉醇洗脱球囊支架、普通球囊支架和粥样斑块切除术在股动脉疾病治疗中的比较性研究
2017-06-06 MedSci MedSci原创
股动脉粥样硬化在外周动脉疾病患者中较普遍。目前,紫杉醇洗脱球囊成形术、支架置入和定向斑块旋切术(DA)为股动脉疾病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对这些治疗手段效果的比较尚未明确。
作者:MedSci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梅斯医学”或“来源: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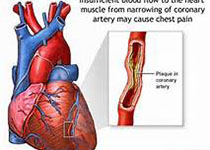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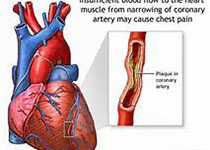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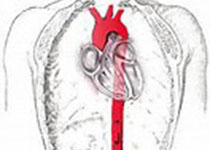





#粥样斑块#
46
#疾病治疗#
53
#切除术#
33
#股动脉#
31
#紫杉醇洗脱球囊#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