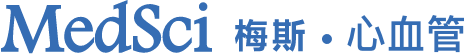我国每年约30万人等候器官移植 仅1/3获得新生
2017-10-27 佚名 方圆
因先天性胆道闭锁而需要肝移植的灿灿与她的母亲张岩。灿灿术后每天吃抗排斥药物,免疫力变得低下,张岩与她接触也必须戴着口罩。“等到了器官就有希望,等不到,一两天的时间内,就是天上地下的选择”,朱志军告诉《方圆》记者。他还不是完全深度的昏迷”,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肝移植病区的示教室内,病人家属小声对医生说着,语气里透着试探,她看着医生,似乎是想从对方那里听到些鼓励和宽慰的话。“我们会
因先天性胆道闭锁而需要肝移植的灿灿与她的母亲张岩。灿灿术后每天吃抗排斥药物,免疫力变得低下,张岩与她接触也必须戴着口罩。
“等到了器官就有希望,等不到,一两天的时间内,就是天上地下的选择”,朱志军告诉《方圆》记者。
他还不是完全深度的昏迷”,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肝移植病区的示教室内,病人家属小声对医生说着,语气里透着试探,她看着医生,似乎是想从对方那里听到些鼓励和宽慰的话。
“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但确实,像病人病这么重的情况,做手术的风险会比较大,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七十,所以你们要考虑好”,主任医师朱志军这样说。
“主要他还是有希望的”,病人的家属又说,她指的是那个“已知的肝源”,通过听医生之间的讨论,她判断出这个肝源很可能来自河北石家庄。
但朱志军心里清楚,手术到底能不能做,要视供体那边的情况而定,而这个环节里变数太多。作为一名从事器官移植30多年的医生,他太了解病人和病人家属现在的这种焦灼心境了。
前段时间,朱志军救治过一名来自云南的肝衰竭患者,病人50多岁,病情要比现在这个病例还重,“肝和肾的功能都不行了,当地医院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但病人的家属没放弃,联系到了这里来,听到朱志军说有一半的救治希望,不想再等下去的家属索性花费50万元包了架飞机,带着病人从昆明一路飞过来。幸运的是,那个病人最终等到了救命的肝源,被救了回来。
“等到了器官就有希望,等不到,一两天的时间内,就是天上地下的选择”,朱志军告诉《方圆》记者。
这种焦灼又残酷的等待,发生在每一家可以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里。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是30∶1。不仅如此,死神留给病人们的时间并不多,“肾衰竭患者尚可通过血液透析的方式多等一段时间,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严重时最多只能等2周,即使是病情稳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3个月”。
“活着真难”
2015年,一部名叫《活着》的电影获得了第9届FIRST青年电影展学生竞赛单元的最佳纪录片奖、二十三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以及第六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大学生作品。片子记录的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病房里那些等待肾移植的尿毒症病人及其家庭的群像。该片让人们了解到,肾衰竭病人对于移植器官的热望及其焦灼的生存状态。
2017年5月,在北京东城区Camera Stylo的小型放映室内,十几名观众观看了这部影片,并与导演马倩雯进行了映后的交流。马倩雯告诉《方圆》记者,她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拍毕业作品期间,看了一则有关器官移植的新闻,才打算走近这个群体的。
电影中,“希望与失望交替,绝望与振作循环”。新的一批肾源来了,护士站外排满了准备抽血化验的病人们。因为都了解那种难挨的心境,病友们会因为同伴配型成功而高兴,同时也会因为自己没能配上而沮丧万分。
患者刘坤鹏表面坚强,实则被一次次配型失败折磨得脆弱不堪。“掰着脚趾头我都想不到我会到这一步”,刘坤鹏对着镜头说。没得病前,他是踌躇满志的创业青年,患上尿毒症后,他亲手将公司关门,流着泪把所有材料当废品卖了,“说实话捅我两刀都没那难受”。“我终于能歇着了”,他这样安慰自己。住到了医院后,刘坤鹏和病房里的病友一样,一边做着透析一边等能够配得上的器官,从此过上了这种“天天盼望幸运之神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生活。
未等到移植器官之前,做透析可以保命。可一位移友(已做完移植手术的人)曾如此感叹,“那种看着血从管子里流进身体里的感觉,没有经历过,就从来不会觉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多么幸福的事”。
病人透析的痛苦,马倩雯亲眼见证过,“两根很粗的针头扎进去,通过一根针把全身的血液和其中的废物从身体里抽出来,再通过另一根针把透析机过滤好的血液重新输回身体内部。他们隔一天就要去透析一次,一透就透四个小时,这种频率能把病人‘扎疯’,因此日常工作得不到保障,生活也都全部打乱。不仅如此,这个过程还伴有各种并发症的可能。有的人透着透着就出现高血压或心脏病,更有严重者透析时出现并发症当时就躺在床上不行了。而换肾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可透析和换肾花费昂贵,能让任何一个普通家庭“一夜回到解放前”。病人付强不忍母亲年纪大了还要在医院伺候她,故意和母亲赌气,从病房里出走,想让她早点回家。伤心的母亲对着众人诉说,“我现在看见大街上要饭的人我都觉得可羡慕”。
14岁尿毒症男孩宋万里的妈妈和刘坤鹏一样开朗爱笑,是病房里少见的暖色。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事重重的女人坐在医院走廊里对着镜头笑着笑着却哭了,她说她“不能倒下”,她的儿子聪明,怕拖累家里,已经好多次想要放弃治疗选择死亡,她必须在儿子面前强装出轻松的样子,以求儿子不要放弃自己。
病人元辉一家实在等不下去,在被医生告知当时不是做手术的最佳时机的情况下,选择在那个春节前做了亲体移植手术,由父亲捐肾给元辉。但术后,父亲的肾在元辉体内出现了排异,面临着被摘除的危险。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重新激活,父亲宝贵的肾只能从他体内摘除然后丢弃。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情绪崩溃的元辉母亲伤心不已,她认为是自己的心急让儿子陷入险境。整个家庭因儿子患病而灰暗,绝望的她曾跑到自己母亲的坟前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活着真难”,这话出自患者白潜郧之口,换肾后肺部急性感染,白潜郧再也没能醒来。他终于结束了那段换肾后排异身体痛苦的日子,却抛下了始终没放弃自己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儿子,以及换肾所产生的一大笔债务。
马倩雯知道白潜郧去世的消息,是在一次纪录片放映交流会上,有个观众问及这些病人的现状,马倩雯回说,“有一些已经做过了移植手术,情况都还不错”。几乎是同时,她感觉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下场时一看,收到的是关于“白潜郧追悼会”的通知短信,“当时整个人就蒙在了那里”。白潜郧的去世对马倩雯的打击很大,“好几个月都缓不过来”。
所以她现在很怕突然接到他们的电话,“不跟你联系,就说明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对于他们来说,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马倩雯说。
协调员的故事
“亲眼看到一个人能救却因为等不到器官而没办法救”,这是身为肝移植医生的吴平最难接受的事情。2000年的时候,他的很多病人都因等不到救命的器官,而一个一个痛苦地死去。2003年,拿到一笔赞助基金的吴平选择去美国匹斯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那里,他了解到国外器官捐献体系的运作。
吴平介绍,与国内器官捐献主要做“因病死亡”的情况不同,美国做“因伤死亡”的情况较多,因为意外死亡的健康身体是最理想的器官移植源。而国外的驾照不仅是开车的执照、身份的证明,也是一份自愿的器官捐献书。如果驾驶员遭遇交通事故,经医生诊断为脑死亡成立,医院便可进行对死者的器官捐献工作。
然而在中国,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影响,刚刚起步的器官捐献工作采取了比西方更为严格几近苛刻的方针——一项捐献行为的实施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公民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一致同意,哪怕捐献者生前曾经在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因此,亲人家属的意见成了影响中国实际器官捐赠的最重要因素。2010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首批人体器官协调员应运而生,肩负起了和潜在捐献者的家庭进行沟通的核心工作,也承载着等候移植器官的患者们的希望。
2014年,吴平正式成为友谊医院中OPO( 器官获取组织 )的一员,拥有了除肝移植医生以外的第二个身份——器官捐献协调员。他开始与各家医院建立联系,期待各家医院的医生们能够在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时候,及时通知到他。
器官获取组织
国家根据《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管理办法,在国家卫计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一个或多个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专门负责人体器官的获取、分配以及维护等工作,简称OPO。
“做起了器官协调员才知道,这活不好干,当医生是人家请求着我做事情,而协调员却是满地求着人家,让人家来同意捐献。但不做这工作又不行啊,没有肝源病人们怎么办?”吴平向《方圆》记者坦陈。
吴平太了解肝移植的紧迫性了,“终末期肝衰竭病人的生死就在几天的时间里,而慢性肝硬化的病人如果等不到器官,就只能看着他们一点点慢慢没了,这个过程对病人来说太痛苦了”。所以吴平拼命地到处跑,“某个医院的大夫一来电话,我们协调员就会过去,几点打电话几点就走,凌晨两三点外出那是常事”。有媒体甚至计算过,器官移植协调员的车子一年下来有10万公里左右,“在路上”是常态。
当现代医疗手段已无法挽救那个病人的生命,协调员们需要及时地介入,在合适的时间段里,慢慢开启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介入的时机很重要,太快了家属们肯定接受不了,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去接受这个事实。但也不能太慢,因为器官捐献的各项手续都需要走严格的流程,太慢了则影响移植器官的质量。”
而在时机未到之前,协调员能做的只有等待,在这等待的每分每秒里,供体的病情变化、家属的态度以及移植器官的质量,都是摆在协调员面前的变量。
“有死者的家属7天内改了6次主意”,吴平感叹说,而因为病情过重导致器官失效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印象深刻的一次,为等一个脑出血病人的签字家属,吴平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到最后却只等来了一句“我们不捐了”。
这些年的器官移植协调工作,吴平总结,往往面对那些已知“器官移植概念”的人们,他们最后同意捐献的可能性会更高。前些日子,友谊医院一个来自贵州的3岁苗族孩子在等待肝源的过程中死亡,孩子的家属在悲痛之余表示,“因为自己清楚等待中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愿意将孩子完好的两个肾捐赠出去,希望能救到别的孩子。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延续孩子的生命”。
“以生命为礼物,点燃他人重生的期待。从捐献那刻起,按下‘停止’的生命,开始重新启动”,吴平告诉《方圆》记者,这是众多等待故事里,最让他受触动的一个。
用亲人的器官去救另一个亲人的生命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系统),是中国器官捐献体系的关键系统。该系统严格遵循国家分配政策,执行无人为干预的自动供受者匹配过程,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器官分配。而当取到“公民死亡捐献同意书”签字的协调员将器官信息录入这个系统后,系统分配程序启动,一条或多条等待的生命将获得新生。
但是,一个月前,在友谊医院肝移植科病房内,因为血型不匹配,新来的肝源却救不了灿灿(化名)的生命。灿灿的妈妈张岩(化名)心急如焚,决定自己给女儿捐肝,做亲体肝移植手术。但是从准备伦理材料、提交伦理委员会到上交到卫计委等审批,完成这个流程最快也要一周的时间,可灿灿的病情却已经不起等待。
张岩怎么也没想到,先天性胆道闭锁,这个每8000至14000个新生儿中仅会发生一例的可怕病症会出现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主治医生告诉《方圆》记者,“胆道闭锁的病因目前不是特别明确,得这种病的患儿最后的表现为肝功能衰竭,肝移植是最好的治疗方案”。
等审批的那段时间,张岩感觉“女儿的生命像是在一天天燃烧”,因胆红素过高,孩子身上已经有了出血点,且肝性脑病的症状也出现了,“意识不清,处于半昏迷状态,即使她睁着眼睛也不看你,你叫她她也听不见”。平日里,医生不仅要给灿灿用药,还需要给她灌肠,灿灿的肚子就胀着,特别大。已经浑身蜡黄色的孩子,从白天哭到晚上,难受地拼命含着张岩的乳头,试图在母亲怀里寻找安全感。心力交瘁的张岩四天没合过眼,精神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所幸3天后,通过医院的加急处理,做亲体肝移植手术的审批终于下来了。张岩和灿灿被推进了手术室,顺利地做成手术。因为灿灿的情况比较严重,术后的她在ICU里住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如今,刚出来不到一个星期的孩子,又因抵抗力太低,感染上了肺炎。
7个半月的灿灿又瘦又小,体重从术前的14公斤,降到了现在的5.9公斤。除了咳嗽,她还在发着烧,为了给她降温,张岩把病床上铺满了水袋。和做过肝移植手术的病人一样,灿灿的腹部留下了两道“奔驰标”一样的疤痕,两条管子仍插在她的身体里,一条是从腹部出来的引流管,另一条是从脖间穿到深静脉里的输液管。因为隔一天要抽一次血,灿灿的大腿和脚上已全是瘀青,小小的她现在还对痛觉不太敏感,但张岩总觉得,“有病的孩子要比正常的孩子懂事些,因为她一看到白大褂就哭”。
手术后,张岩为灿灿制作了表格,记录每天吃奶、吃药、喝水和排便的情况。
所有抗排斥药物都要磨碎了冲水,再用喂药器给灿灿喂进去。得了这种病,灿灿终生都要服药。未来的生活是张岩能想象得到的,“孩子稍大一点吃药肯定会哭,还会面临各种并发症的可能”。
术后的张岩一直肝区疼痛,在操劳孩子的同时,一起陪床的丈夫不忘每天给她后背按摩。因为孩子这病,这个家庭开始了“车轮战”的生活,“倒班”休息的地点则是医院对面的宾馆。这种一直住宾馆的状态,要持续到孩子身体恢复好,能够出院的那天。
灿灿邻床的病友是一个从河北来的2岁男孩,最近因代谢病做的肝移植手术。肝移植术后,即便是出了院也要求每周一次复查,那些在北京没有家的病人家属们,几乎都选择了在医院附近租房子住。家里人得了这样的病,意味着一辈子都离不开医院,比起那些日日都很艰难生活的人们,张岩感觉自己的情况要好得多,所幸自己和丈夫在北京有家、有体面的工作,孩子的病虽负担沉重,但于他们而言还算能支付得起。
据《方圆》记者了解,虽然目前肾移植的术前和术后、肝移植的术后都已纳入医疗保障,但这些费用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仍旧是不能承受之重。
幸运的人
两年前,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的政策令一些人感觉“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来了”。有等不及的病人抱怨,“写在纸上的法律反而简单”,在纪录片《活着》里,病人们也不止一次表达出这种不安的情绪。
“当然不能用乐观的状态去比较病人们的‘忍受’”,吴平说,但他对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现状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在国内死去,要求捐献出自己的器官,我们这边却几乎不知道这个概念,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个程序。而如今,在我们如此人口基数的大国里,每年器官捐献的数量已经从开始仅有的十几例,上升到了九千多例”。
“而比起以前,现在的等待者们等到器官的希望更大了。一方面,随着器官捐献宣传工作的进行,国人对器官捐献认知的提升,我国成功捐献的案例几乎呈每年翻一番的速度,且将来还会更多;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造器官的功能越来越完善,未来会更好地解决人体器官短缺这个问题。”吴平告诉《方圆》记者。
在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的办公室内,《方圆》记者了解到,国内肾移植率比2015年增加了28.1%,而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肾移植率又比2016年上半年上升了21.6%。这意味着半年内已做了4956例肾移植手术。“如果是呈这样一个上升速度的话,今年也许有望达到1万例左右”,石炳毅告诉《方圆》记者,近两年器官移植在数量上发展迅速。
乐观数据的背后,是幸运的降临。在清华大学后勤部工作的吕宏杰,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幸运的人”。56岁的他刚做完肝移植手术,“几乎一天也没有等”。
4月里的一天,吕宏杰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医生告诉他需要等合适的肝源再做手术,“最多要等3个月的时间”。从医院里回来,担心等不到肝源的吕宏杰打算多去几家能够做肝移植的医院排队。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下午4点多回到家里,他就接到了302医院的电话,通知他当天晚上去住院,准备第二天一早的手术。
吕宏杰当时就有些蒙,“没想到能这么快”。手术后他打听,原来这个肝源本来匹配给另一个女患者,但女患者体重较大,供体器官的大小与其不匹配,此器官源又退回到网上做重新分配,而依据器官分配的“就近原则”,适合移植条件的吕宏杰最后做成了手术。“看来我和这肝有缘”,吕宏杰说。
现在,正在恢复身体的吕宏杰在家静养。通过熟人的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器官移植受者的微信群,经常和群里的“移友”们互动。移友们都来自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联谊会会长李祖澄,也曾在十几年前接受过肝移植手术,到现在身体很棒,国庆节之前,李祖澄还组织了移友们去朝鲜旅游。
吕宏杰感谢这次人生偶然的馈赠,能够让他走向新生。但有时他也会“胡思乱想”,“怕术后会发生感染,也怕长期服药的身体出现一些并发症”。就在上个月,一个比他早一个星期做成移植手术的病友因胆管阻塞去世,这样的消息时刻影响着他脆弱的神经,“还是一切看命吧,我如果能活得像李祖澄那样,也就值了。”吕宏杰说。
作者:佚名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梅斯医学”或“来源: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